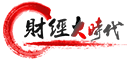作者|蓝字
原创首发 | 蓝字计划
山城重庆,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
在这里,曾经出现生态灭绝般的捕捞。
最后的长江渔民们,组成的反盗猎巡护队,在奔流的大江上穿梭。他们,曾和盗猎分子的船只相撞,曾被打得满脸是血,也曾被人们天天盼望着“因为贪污被抓了进去”。
伴随着整个长江系统的立法保护,冲突似乎更被推到了极端。
长江沿岸(图片来源:蓝字特邀摄影师梁清)
从渔业保护切入,到鱼苗培育、支流与采石场的管控…再到数字化公益和社会力量的介入。政府渔业、民间护渔、腾讯公益平台、公益机构和中国网民等,无形中卷入保护长江,成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人间图景。
图景里,是一个个与洪流相争的鲜活生命。
过去的几十年里,老罗一直以为自己会在水上漂到死为止。
从记事起跟父亲学打渔,三张草席搭起小木船;麻绳拴成的渔网,要用猪血来浆,再烧柴火晒干,熏得双眼流泪;每天天黑撒网,天亮收网。奔流不息的长江,见证着他迈入婚姻、孕育子女……脚下的船从小木船换成铁皮船,后来铁皮船又换成不锈钢大船。
在这艘船上,他的母亲生下了他们兄弟几个。老罗的哥哥,在7岁的时候,跟着奶奶在船沿打捞江面飘过的木柴,失足掉进了江里。年迈的奶奶看着哥哥在江里浮沉挣扎,越飘越远,再也没有回来。
现在,这艘大船上了岸,和旁边十几艘渔船一起等待被销毁。渔民们手持牌照在船前拍照登记,为捕鱼生涯留下最后的记忆。紧接着,工人们忙碌起来,气焊枪、铁锤轮番上阵。用不了多久,这堆残骸会被融化为红彤彤的钢水,再凝固为一堆锅碗瓢盆。
养了七年的狗“雷雷”对周遭的变化毫无察觉,有馒头吃就欢天喜地。薄雾散去后,对着空荡荡的江岸,63岁的老罗自顾自哭了起来。
浮沉半生,以船为家,他早已习惯每晚晃晃荡荡地入睡,仿佛母亲推着摇篮一样。洪水汛期,将船拖入避风港,看着奔涌的江水东去,心也跟着变得辽阔,所有苦乐仿佛都融入其中。
停泊在码头边的渔船(图片来源:蓝字特
邀摄影师梁清)
将他和近30万渔民推到陆地上的,是长江流域史上最严禁渔令,自2021年1月起正式实施,为期十年。禁捕范围纵贯长江上中下游,青海、云南、四川、贵州、甘肃、陕西、重庆等14省市都被囊括在内。对世代“以水为田”的渔民而言,政府发放补贴,提供技能培训都难以彻底抚平他们对新生活的忐忑。
但靠水吃饭这么多年,他们也明白,长江早就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即使不转产,今后也将无鱼可打。
“我年轻那会儿,站在船上就能看到大鱼在水下游动,黑乎乎一大片。爷爷教我‘手打网’,随便一张网下去,都能打几斤鱼出来。”
长江边长大的刘鸿,是个捕鱼能手,在他的记忆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传统渔业的黄金时代。那时候码头少、货船少,岸边芦苇摇荡。舀一瓢江水,加点明矾就能喝,入口清甜。渔民们遵循着“取之有度,顺应自然”的朴素道理,抓大放小,吃喝不愁,每年赚的钱比当地人均收入还高出不少。
可当新的世纪来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长江沿岸平地起高楼,上游的林地、草地面积则明显减少,中下游湖泊、湿地大面积萎缩。
与“长江大开发”相伴的,还有采砂泛滥。江西师范大学鄱阳湖湿地与流域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15年发表在《地理学报》上的一篇论文显示:非法采砂船以柴油为动力,造成水体石油类污染急剧增加;通江河道的过水断面扩大,加快了湖水注入长江的速度,使枯水期提前、延长,打鱼周期被大大缩短。
鱼没有从前好打了,心思活络的人开始追求效率更高的捕鱼方式。
最早的电鱼者从家里拖一根电线到邻近水域,用220伏的生活用电进行电鱼,杀伤力有限。经过多年的“技术迭代”后,如今的电鱼机已经用上了二极管、三极管、可控硅作为核心元件,可调节频率的同时,输出电压能达到上千伏。
“光江津区就有200多条电鱼船,四五百名非法电鱼者,这些人不分白天黑夜,这拨走了那拨又来了。”
把绑着电极的线杆从船头伸入水中,水面立即泛起白色的浪花,范围达到两三亩地。几乎一眨眼的功夫,几百条鱼翻着白肚浮出水面,毫无知觉,任人捕捞。这是长江上最常见的电鱼作业。
除此之外,电鱼还有更繁杂的“大工程”。两条渔船拉起一张电网,与江面等宽,协同前行,缓缓划过水面。电网释放的瞬间电量足够电倒一头牛,所到之处,不分种类,不论大小,鱼都被一网打尽。要么顷刻间毙命,要么因为性腺发育受损丧失繁殖能力,已经产下的卵也不会孵化。
非法电鱼船
电流通入水体后,耗尽一定水域面积内的氧气,导致水体真空。因电击或窒息而死亡的水生生物沉积水底,腐烂变质。严重的会造成某一水域食物链断裂,自然水域的生态平衡被彻底打破,“死水”现象因此而成。
鲤鱼40元一斤,花白鲢60元一斤,黄辣丁150元一斤,江团300元一斤,岩鲤400元一斤,长江鲟和娃娃鱼价格更是不菲……这种断子绝孙式的捕捞方式,为偷猎者带来了极为可观的收入。一晚上随便电几百斤鱼,选一处隐蔽的岸堤,迅速与收鱼人完成交易,再由厢式货车冷链运输至外地,销售给长期合作的水产摊摊主,最终转卖给饭店或个人,年入百万是稀松平常的事。
《长江保护法》出台之前,行为人在禁渔期、禁渔区之外非法捕捞大多只会收到行政处罚。即便罚款,金额也不过几百至几千。犯罪成本跟高额利润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里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可以赚钱的金矿,挖空了、挖没了,换个地方继续挖就是了。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截然不同的。”
旧的秩序轰然倒塌,很多渔民出于对长江的感情,不愿意顺应潮流,只能眼睁睁看着收入大幅缩水。
▲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江津区转业渔民(图片来源:蓝字特邀摄影师梁清)
很多年以前,老罗甚至打到过30多斤的花鲢。但17年以后撒一次网,捞上来的几乎都是垃圾——巨大的渔网在台阶上堆成高高的一座山,一座长满了塑料瓶、塑料袋和枯枝败叶的五彩斑斓的山。他和老伴需要花一下午的时间才能把这些垃圾清理掉。
经过捕鱼黄金时代的长江,剩下的,是鱼类的黄昏。
曾经,长江是淡水鱼类资源最丰富的流域,盛产多种经济鱼类,高峰时期曾占到全国淡水捕捞总量的60%。可到了2019年,生物完整性指数达到最差的“无鱼”等级。青、草、鲢、鳙“四大家鱼”的资源量大幅萎缩。缺少了鱼类,水藻因为没有天敌的牵制而疯狂生长,水中杂物越来越多,水域生态不断恶化。而长江作为国内第一大河,每年需要供给约4亿多人饮水,影响多大可想而知。2020年初,白鲟灭绝的消息更是将长江水生态系统的溃败以最惨烈的方式推到公众面前。
中国淡水鱼之王长江白鲟
事实上,国家层面对长江流域的危机早有察觉,自2003年起就启动了春季禁渔制度。
然而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看来,对于渔业资源急剧衰退、珍稀动物日益濒危的长江来说,“季节性禁渔“治标不治本,效果十分有限。
2004年,曹文宣让学生到多地进行实地调查,学生们发现,禁渔期结束后,渔民捕捞上来的鱼多是当年出生的十厘米左右的幼鱼。这意味着,几个月的禁渔期,仅仅让一些鱼类有了产卵机会,但是孵出来的幼鱼还没来得及长大就夭折了。因此,鱼类种群难以繁衍壮大。
从2006年开始,他坚持通过多种渠道呼吁在长江流域禁渔十年。
“十年禁渔可以让鱼类有相对充分休养生息的时间,以四大家鱼为例,它们的野生种群基数本身已经很低,繁殖量有限,成熟期一般需要四年,十年时间可以给它们两个世代的繁衍期。”
接踵而至的,是被期盼了近20年的《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流域立法,它将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到了压倒性位置。
没有人知道,各方势力的撕扯,将要在长江掀起怎样的风浪。
《长江保护法》落地的第一天,重庆市相关单位在大梁子码头进行法制宣传,并且集中销毁185件收缴的非法捕捞渔具。
官方态度很明显,想以此震慑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行为。但长久以来,在非法捕捞者眼中,渔政等执法单位都是“纸老虎”一样的存在。
集中销毁非法捕捞渔具
长江江津段长127公里,江面宽700米至1500米,而渔政执法人员却不到10人,人力严重不足,常常顾得了头顾不了尾。接到举报电话不能及时赶过去,就会被群众批评不作为。
由国家统一采购的渔政船,弄得像旅游观光船一样,虽然配套完善,但速度慢,只能走长江中间,无法在浅水航行,容易暴露又不灵便。加上没有夜航功能,只能白天晃一圈刷一下存在感,一到晚上就彻底歇菜,根本不被电鱼者放在眼里。
曾经在江津区渔政站担任站长的李荣向记者诉苦,为了打击非法捕鱼绞尽脑汁,甚至一连几夜蹲守,但依然无功而返。他们一年办不了几件案子,不是不想办,而是太难办:设备跟不上,人员跟不上。实际上,不只是江津,长江沿线各地的渔政部门都面临相似的困境。
上级问责、群众埋怨,夹在二者之间,压力越垒越高。
2014年4月,江津渔政人员按照惯例到油溪镇老洼沱码头增殖放流。在岸边看热闹的刘鸿忍不住调侃:“你们现在放鱼苗有什么用?过没多久就被电死了。”
李荣听到这话,抬起头来对刘鸿说,“你看到了就抓现行,抓了送过来给我们处罚。”
刘鸿水性好,当过兵,又对电鱼者积怨颇深。之前为了招待朋友,想着开船打点江鱼,结果整个下午一条鱼都抓不到,去找渔民买,渔民也很无奈,“鱼都被电鱼的搞光了,哪还轮得到我们。”
被朴素的正义感驱动,当天下午,刘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义务巡护。
独自开着7.6米长、40马力的汽油船巡至麻纱桥水域时,发现有两个开柴油船的人在增殖放流地点附近公然电鱼,刘鸿一边掏出手机录像,一边全力追赶。
好不容易把船逼到岸边,没想到对方突然调转方向,加大马力撞过来。船身剧烈摇晃,刘鸿一个趔趄跌入江中,但就在落水的一刹那,凭借良好的水性,他抓住对方船舷一跃而上。
鸿鹄志愿队队长刘鸿(图片来源:蓝字特邀摄影师梁清)
俩人见刘鸿高大魁梧,身手又如此矫健,一时之间没了主意。船头的人跳水逃跑,船尾的人则束手就擒。
刘鸿当场缴获了电鱼工具和渔获物,将非法电鱼者移交当地渔政处理。后来,弃船逃跑的那名电鱼者同伙,也投案自首。
上岸后,刘鸿总结了两条教训:一是非法捕捞船的硬件设备都很先进,巡护船要更结实、跑得更快,才能逮住嫌疑人;二是要有得力的团队,至少两人协同作战,才能避免更大的危险。
当时刘鸿在家乡油溪镇经营一个专门做古建筑安装和建造的公司,手头积蓄颇丰,他决定自费购买装备,组建一支民间护鱼队——重庆鸿鹄护鱼志愿队。刚开始缺人,他就直接抽调公司的员工一起出去巡护。
鸿鹄志愿队的大本营,是队长刘鸿的洪江古建筑公司(图片来源:蓝字特邀摄影师梁清)
几年后,退捕上岸大潮席卷而至,熟悉水域环境的渔民渐渐成了志愿队的主力军,56岁的陈永彬就是其中之一。30多年的捕鱼生涯里,他将“克制”视为最大美德,对酷鱼滥捕者嗤之以鼻,每次发现都跟渔政部门举报。站长李荣觉得他有正义感,不怕得罪人,便将他推荐给刘鸿。
当时陈永彬拿着政府给的二十几万补贴住进新房,吹不到江上自由无拘的风,整个人就像养在玻璃缸里的鱼一样,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做生意怕亏本,当保安又嫌太无聊。思来想去,加入志愿队,换一种新身份与长江日夜相伴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一次巡航过程中,在长江石门镇苟洲坝附近,抓住3名电鱼者,当场查获渔获270斤,另外还有500多斤鱼被藏在下游的一处土坑里。那些都是正在产籽的江鱼,一个个挺着大肚子。陈永彬感觉心被狠狠揪了一下,眼泪差点滚落下来。
最本能的情绪反应告诉他,这事有意义,值得花大力气去做。可对于将来会被卷入一个怎样复杂的旋涡,他还想象不到。
▲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鸿鹄志愿队队员(图片来源:蓝字特邀摄影师梁清)
人家偷鱼,他们护鱼,断人财路,又拿不出执法资质,久而久之自然就成了电鱼者的眼中钉、肉中刺。不服气的人越来越多,拉帮结派地对付他们。
最惨烈的一次,是在2015年正月初三。大家还沉浸在热烈的春节气氛中时,刘鸿接“线人”报告,有人在苟州坝撒网捕鱼,他立即带上一名队员赶去拦截违法船。捕鱼者丢下渔具掉头就跑,正当他们清理现场时,那人却带着二十余人过来将他们团团围住。好些都是醉汉,下手不知轻重。混乱中,队友被打得趴在江边,刘鸿头部被鹅卵石砸中,顿时血流如注,但他仍死死扭住对方,直至警察赶到。
当晚回到家,刘鸿头缠纱布,衣服遍布血渍。妻子被他这幅尊容吓得不轻,砰一下把门关上。他在外面解释半天,才被放了进去。
打击非法捕捞,渔政部门需要民间力量的补充 但又不能直接让渡执法权。无奈之下,便给鸿鹄志愿队每人发了套巡护队的制服,打擦边球,半官方地让他们进行巡护。按理说,他们取证后交由渔政执法即可,但在具体操作中,取证技术有限,渔政力量跟不上,只能他们亲自扭送。
并非每个人都会被他们那套制服吓得束手就擒,碰上不配合的,免不了有些肢体冲突,通常刘鸿会和队员强行将人拽到船上,再押送至公安机关。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操作显然越俎代庖了,别人要是较真起来去告他们,一告一个准。
不得不承认,尽管志愿队与长江有深刻的情感联结,也通晓水性,熟悉各种鱼类,但在具体的巡护过程中,他们的操作模式却是“事倍功半”的。就连工作日志和和案宗记录都坚持手写,处处透着前现代的古典气息。
鸿鹄护渔志愿队半年来的工作日志和总结文件(图片来源:蓝字特邀摄影师梁清)
而偏偏长江保护,又是一个系统化的、涉及面极广的大型工程。除了上中下游、还包括江河湖库、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而打击非法捕捞之外,鱼苗培育、拦河筑坝、挖沙采石也都在治理范畴之内。
像刘鸿这样的民间游击队,面对如此宏大的议题时,难免显得费力不讨好。无法用团队力量撬动更多资源,还经常因为信息不够透明而被质疑贪腐。
坊间流传他们白天护鱼,晚上偷鱼,之所以把船改造得这么好,是为了偷鱼时不被抓。毕竟人都是逐利的,“如果捞不到好处,护鱼队这么拼图啥?”甚至还有人对他们进行盯梢,看到他们开船出动,就给渔政或公安部门打电话举报。
为了驱散谣言,志愿队只能和政府“蹭关系”,假装自己已被收编。每当别人质疑他们“无利不起早”时,他们就故意放话,“是呀,我们每月从政府那里,可以领三四千块工资呢。”
那时候刘鸿和他的队友们还不知道。进入信息爆炸时代,浪潮的方向早已转变,互联网对公益范围的扩展和效率的提升作用日益显现。
作为中国互联网三巨头之一,如何利用自身传播优势,帮助民间公益组织拥抱技术潮流,以透明流程,建立合理高效的信任机制,是腾讯公益一直关注和努力的方向。
在不被公众看到的前五年,鸿鹄志愿队不但没有收入,还一直倒贴钱。
没有互联网技术和数字化工具的介入,他们纯粹用肉体凡胎为长江珍稀特有鱼类织成一道防护网。
在长江打渔要紧跟潮水动向,落潮时撒网,涨潮时收网。有经验的老渔民都知道,夜晚是捕鱼的最佳时机。为了掩人耳目,非法捕捞者自然更喜欢夜间出没。于是上千个夜晚,刘鸿和队员都在江面上度过。
三面朝水,一面朝天。为了不影响视线,船舱没装顶棚。一脚油门下去,船尾浪花沸腾般翻滚,江风凛冽,裹挟着细沙和水珠,声势浩荡地扑向船上的人。时间长了,脸被冻得几乎失去知觉。持续不断的马达轰鸣声,和风声纠缠在一起,催眠效果奇佳。必要时,刘鸿得狠狠掐自己一把,以免被困意俘获。
▲左右滑动查看更多
志愿队夜巡(图片来源:蓝字特邀摄影师梁清)
夜间巡航,最怕的是打草惊蛇,因此确定目标前,必须关掉一切光源,甚至连手机屏幕都不能亮起。零散分布的航标灯是深夜唯一的指引。红色表示浅滩,绿色代表礁石,两灯之间为航道……置身于浩渺江水之中,驾驶者必须对周围环境保持高度警觉,一边搜寻偷猎者的踪影,一边根据航标灯的变化判断水势急缓,以及水下是否有礁石。
刘鸿管航道距离最窄的地方叫做“母猪号”,因为水凶得就像母猪发情一样,漩涡连漩涡,波浪推波浪,重重撞击船身。人被从座椅上高高弹起,又猛地回落。几番颠簸之后,犹如风中凌乱的树叶,骨头都快散架。
志愿队每次向下游巡航100公里到珞璜,大概花费三至四小时;向上游巡航最远可以进入四川宜宾,经过边界就用江水洗把脸,稍作休息。
等待非法捕捞者现形需要极大的耐心。最夸张的时候,他们要在江边草丛躲藏两三天,即使下雨也不离开,几人轮班值守。“吃饭都是别人送进草丛里。”然而那些人比想象中更狡猾,为了防侦查甚至会牵着猎狗到江边来,一旦藏得不好被对方发现,几天的忍耐就都前功尽弃。
刘鸿在长江岸边的草丛里,搜捕偷猎者(图片来源:蓝字特邀摄影师梁清)
实际上,利用高科技手段,南京政府已经找到了效率更高的解决方案。遥感卫星“千里高空看长江”、亿级像素相机“千米之外看江豚”、全天候监测长江南京段非法捕捞船只和防控船舶污染,实现实时感知、数据汇集、智能分析、跟踪预警等功能……形成从问题发现预警,到现场处置反馈的完整闭环。
大量时间精力花在护渔上,刘鸿建筑公司的经营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而无底洞般的金钱投入更是让整个家庭如履薄冰。
“人家电鱼船更新换代,我们就得跟着提档升级,不然根本抓不住。” 为了使护鱼船更坚固、速度更快,他们多次进行改造升级——船身从铁板到不锈钢,再到后来的胶板、铝合金;发动机从30马力到40马力,再到后来的60马力、90马力,甚至150马力。每换一次发动机,花费至少10万起步。
马力越高越费油,出去一次要消耗6桶共计240升的汽油,花费两千左右。几年来快艇坏掉的螺旋桨也堆了一地,每换一个至少两三千。
《长江保护法》出台之前,非法捕捞的犯罪成本很低,有时候辛辛苦苦把人扭送到公安局,结果对方罚的钱还没有他们跑一趟的油费多。
这样的情况见多了,难免会怀疑苦苦坚持的意义。每天日夜颠倒,四处树敌又赚不到钱。说自己在行正义之事,可实际上很多操作都不符合程序正义。这期间,有队员经不起诱惑接受了非法捕捞者的利益输送,临阵倒戈,每次巡查前都给他们通风报信,被刘鸿发现后清除出队伍。
小镇本就这么点大,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活在熟人关系网络里,像刘鸿那样拉得下脸面,碰上亲友也照抓不误是很难的。承受不了这种压力的队员,只好主动离开。
原有22名队员的护鱼队,最落寞时仅剩7人。
巡护完上岸的刘鸿,跟河边玩耍的孩子打招呼(图片来源:蓝字特邀摄影师梁清)
刘鸿的妻子本来挺支持他的“长江保卫战”,但受到疫情冲击,公司很多项目迟迟没能回款。眼看经济问题越来越严峻,逐渐成为家庭的主要矛盾,她也忍不住向丈夫施压。这一次,犟脾气的刘鸿没有再死磕下去。当初一腔热血扎进“护渔大业”,几年下来,在没有任何补贴的情况下,总开支竟已超过200万。万里长江,渔政管不过来,加上他的志愿队,也依然力有未逮。十几个人互相打气,用爱发电,年深月久还是免不了疲软。
他们就像新时代的“公益民工”,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更缺乏良性的,能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去推动的模式。
队员收缴渔具(图片来源:蓝字特邀摄影师梁清)
意识到这点后,刘鸿陷入深深的挫败之中。停止出船的两个月,非法捕捞者重新猖獗起来,案件数量大幅反弹。一想到过去几年的努力就要功亏一篑,他不由自主地又坐回到巡护船的驾驶位上。本来这次是带着“过河卒子,退无可退”的悲壮感重新上阵,没想到,转机却终于出现了。
去年4月1日,重庆市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与鸿鹄志愿队签订购买服务合同。利用这笔资金,队员们买了五险,每人每月还能领到500元补贴。紧接着由保护处牵头,志愿队和阿拉善SEE重庆项目中心达成合作,收到30万的资金扶持。
这笔钱基本可以覆盖一整年的大部分支出,但今后若想以更加专业,效率更高的工作方式开展流域范围内的协助巡护,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
比如没有执法权,不能强行扭送、限制非法捕捞者的人身自由,但是借助远程抓拍仪、无人机、红外线夜视仪等设备,可以更隐蔽地完成取证工作,锁定完整证据后通过支援渠道调动警力支持即可。
刘鸿曾经见识过一款智能化程度很高的无人机,航程可达20公里,能够避开电线,在200米的高空上还能识别二维码,对保护长江支流大有裨益。但20万的价格让他望而却步。
传统的公益支持,缺乏持续的造血能力,能够实现的资金额度十分有限,而且因为受助方、捐赠者、公益机构三方无法建立连接,信息流通不畅,始终存在信任“黑盒”。互联网公益的介入,以平台为基础,以数字化为动力,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
健康的公益,不能纯粹靠个人英雄主义驱动。像鸿鹄志愿队这样,就是一个孤胆英雄式的民间游击队案例。宣传不够,透明度有限,在大众中缺乏认知度。尽管用情怀能够感染身边一些人加入,但效率低下,耗时耗力,队员需要全职投入,又没有稳定收入。即使已经得到阿拉善的资助,但长远来看资金维系也极为脆弱。所以,它需要形成一种可复制的运作模式,感召更多人参与,吸引更多社会组织赋能,让善意持续破圈,从而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已连接超4亿人次网友的公益平台,腾讯公益早已打破筹款难的僵局,通过区块链的电子认证,使得捐款过程的数据无法篡改、不可伪造、可以追溯、公开透明,同时也有效解决了数据流通共享过程中的安全问题。
唯有打通信息,带公众走出信任黑洞,困扰民间“游击队”的种种问题才会不攻自破。
十年禁渔为众多长江水生生物提供了恢复种群的机会,但还不足以让它们彻底摆脱生存危机。
加快长江水生资源量的恢复,增殖放流(向长江投放鱼苗)就是手段之一。
志愿者往江中投放珍稀鱼苗(图片来源:蓝字特邀摄影师梁清)
随着学界力量的介入,增殖放流由以前的“以主观愿望为主”变得更精准更科学化。在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对整个生态系统进行分析,缺了哪个层级就针对性地补充哪些,贴近实际需求的同时,放流的物种和数量也不会对流域本身生态系统造成大的扰动。
与恐龙同时代的长江鲟,作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已被列入极危级(CR),为了确保放流效果,阿拉善SEE重庆项目中心采取科学监测和人工巡护两种举措。
首先在长江鲟体内植入电子芯片进行标记,然后在鸿鹄志愿队的巡逻船上安装超声波接收仪(VR100),收到信号后,仪器发出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并显示出亲鱼的PIT编号,GPS记录追踪轨迹。这种方式可以实时监测长江鲟亲本的生命动态,身处何地以及周边环境。
数字公益化的道路上,现实也常常跟预设产生偏差。工作人员曾经碰到过鱼苗放流两周后接收不到信号的状况,跟厂家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虽然电池可以支撑三个月,但是芯片本身却只有半个月有效期。
“虽然我们放流了很多鱼类,但通常情况下,鱼儿会将卵产在江边岩壁的青苔上,因其附着力不强,被水流冲散后会大大影响成活率。”重庆市林业局一负责人告诉蓝字计划,”而人工鱼巢恰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根据鱼类繁殖习性,志愿者们将水游草捆扎成束,一束束用竹框架固定起来,再将一个个这样的竹框架投入江中,用竹竿连接成网格,人工鱼巢就建成了。它能起到水草的作用,粘附性强,还能避免其他天敌的袭扰。同时,由于靠近岸边,远离主航道,既利于鱼卵孵化,也不会影响正常航运。
人工鱼巢(图片来源:蓝字)
每年三月至六月,是长江上游鱼类集中产卵和繁殖的时间,“在人工鱼巢里随便套一张网都能抓个一两百斤,等于我们前功尽弃。”为了避免被非法捕捞的人盯上,护渔队每天晚上都会去这里彻夜值守。
事实上,竹竿扎成的人工鱼巢并非新近发明,刘鸿小时候就见到许多渔民通过这种方式获取鱼苗,只是当时大家完全沿袭祖辈们“靠天吃饭”的思路,根据个人经验以及对水流的了解在相应的地方设置鱼苗培育,对于存活率和失败率毫无概念,只能凭感觉猜测。
而如今, 在西南大学的技术支持下, 鱼类在人工鱼巢中的适应程度和遗传多样性都可以被进一步了解。
水下机器人的应用,能够摸清鱼卵的密度、孵化率,适宜孵化温度等指标。经过反复改进之后,1万平方人工鱼巢可以产出7000万尾鱼苗,存活率达40%以上。
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数字。
实际上,公益数字化不只体现在资金募集以及器材升级上,它的本质在于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数字化工具最大程度地整合资源,推动庞大的公益项目达到几何倍数的效果。
2021年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即将召开。如何将数字化公益进一步纳入公益事业发展体系,映射到各个维度上,构建新的蓝图,自然会成为参会各方重点关注的议题。
如果说“情怀”二字早已沦为破解社会痛点时处处掣肘的遮羞布,那么负责任的数字化,就是这个时代科技公司对公益最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李思阳
原标题:长江暗战